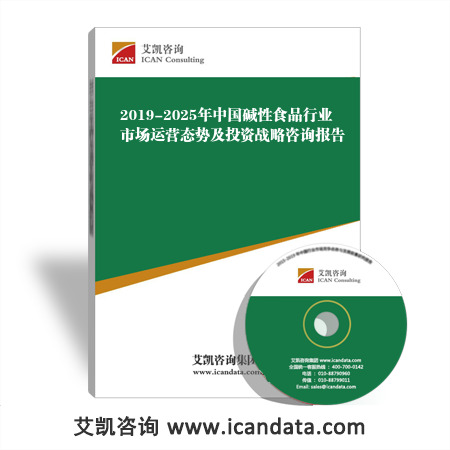导读:20年前的3月26日,海子在山海关至龙家营的一段慢行铁轨上平静地躺下来,一列呼啸而来的火车从他身上决绝而去时,海子身边携带的四本书:《圣经》、梭罗的《瓦尔登湖》、海涯达尔的《孤筏重洋》和《康拉得小说选》在接近黄昏的暮色中剧烈的翻飞,那一
20年前的3月26日,海子在山海关至龙家营的一段慢行铁轨上平静地躺下来,一列呼啸而来的火车从他身上决绝而去时,海子身边携带的四本书:《圣经》、梭罗的《瓦尔登湖》、海涯达尔的《孤筏重洋》和《康拉得小说选》在接近黄昏的暮色中剧烈的翻飞,那一幕宣告了一个时代精英诗人的死亡绝唱。那一天既是海子的祭日,也是他的生日。那一年,海子25岁。
那时候的我还只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小女孩,读着似懂非懂的诗文,读到的只是遥远和迷惘。
直到进了大学,和三五好友经营文学社,写诗,写文,读那本黑色封面的《朦胧诗选》,读北岛、顾城、海子……读到了“从明天起……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温暖。海子诗里的纯净和力量,经常让我在青春激扬的日子里内心奔涌着泪水和忧伤。
20年只是弹指一挥间的过隙,20年后的今天,海子刚刚45岁,也许正是一个诗人最顶峰的创作年龄。但是,如果20年前的那幕悲剧没有发生,如今人到中年的海子是否会成为诗坛的巨匠?中国是否将成就另一位惠特曼或者狄金森?
诗人叶匡政在《不敢怀念海子——海子二十年祭》一文中说:“20年了,我依然不敢怀念他。读他的诗句,就会看到自己人到中年的污浊与卑微。我们的青春、我们血液里的诗人,竟被尘土和世俗掩埋得那么深。怀念他,只有让我更加羞愧。”
忽然感觉这就是一种宿命,上帝在赋予艺术家以才华的同时,总是也赋予他们痛苦。很多艺术家用自杀的方式来完成自己对艺术追求的极致飞跃,比如叶塞宁,比如凡高。死亡,并成就艺术的永恒,这似乎成为了他们的使命,用死来表达自己不能苟同于世俗的社会,用死来解脱自己根深蒂固的灵魂之苦。而活着的人又因为他们的死给予了他们更神圣的光环:“为诗歌献身”、“殉道者”,使他们的死成为一个具有精神象征意义的事件,就如同春秋时期很多铸剑师自己跳进炉中,认为剑是需要人血的,所以用自己的身体完成了最后的作品。
海子的生前好友西川曾经这样评价过海子:“海子只生活了25年,他的文学创作大概只持续了7年,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里,他像一颗年轻的星宿,争分夺秒地燃烧,然后突然爆炸。”
前几天读一位刚去海子家乡安徽祭拜过海子故居的朋友写的文章,三月的怀宁县小山村查湾,漫山遍野的清明花正开得灿烂,而海子年迈苍老的父母依然在这个封闭而贫穷的小山村里守着寂寞,守着20年以来丧子的巨大悲痛。
读到这些文字,我心灵总是悸余不已,海子的父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他们曾经为15岁就进北大读书的海子骄傲过,他们一定不曾理解“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带给海子的心灵顿悟,他们更不曾理解当大学老师的儿子为什么要燃烧?又为什么要爆炸?
我也不曾真正理解过海子,理解过他为什么要用自杀这种方式来表明灵魂的追求,为什么要在自杀中完成其最纯粹的生命言说和最后的伟大诗篇。
我更不曾理解海子为什么要燃烧?又为什么要爆炸?我们的灵魂纵然积满厚厚的尘土和世俗,纵然在污浊和卑微里谀谀前行,可是我们依然勇敢的用自己那颗敏感而脆弱的心去看世界,去体味人世,去选择、并全身心地接受现实生活。其实,好好对待生活和生命,是对自己,更是对那些爱你的人的最大尊重。
海子,只是我们白衣飘飘的青春年代里忧伤的符号。
为什么理解只是符号青春海子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