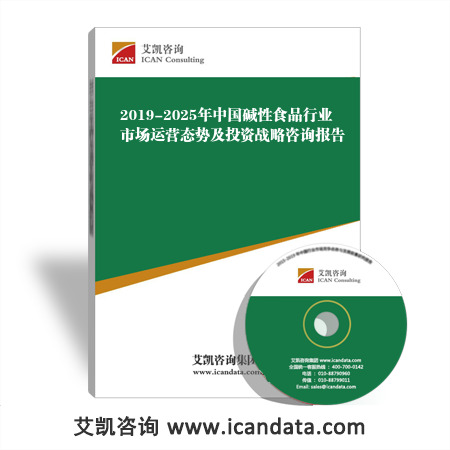导读:编者按 为什么可以不问质量、不问功能、不问价格,只要是苹果的产品,就会引发市场地震? 为什么无论是笔记本电脑还是打印机、服务器或是软件,只要是IBM的,就意味着可信赖? 为什么数十年不更换包装、不更换口味,可口可
编者按 为什么可以不问质量、不问功能、不问价格,只要是苹果的产品,就会引发市场地震? 为什么无论是笔记本电脑还是打印机、服务器或是软件,只要是IBM的,就意味着可信赖? 为什么数十年不更换包装、不更换口味,可口可乐仍然可以卖向全世界? 这是品牌的力量。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内,中国内地曾经诞生了很多中外合资企业和民营企业,而今天真正被后人记住的本土品牌,特别是IT品牌却屈指可数。经历多次变革的中国IT企业品牌鲜有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并未成就像IBM、惠普、苹果、英特尔那样的优秀品牌,我们忍不住扪心自问:为什么? 本报将推出系列报道,把目光投向30年来中国IT品牌的兴衰沉浮,试图通过回顾历史和展望未来,为产业提供一份思考。本报还将启动《值得期待的新兴品牌》等报道,敬请关注。 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国IT产业30年。30年来,有数量众多的中国企业一度叱咤风云,却突然销声匿迹;有的曾经满目繁华,现在却硕果仅存。他们中多数曾经有显赫的名声,却并没有真正长大。究竟为什么呢? 2008年,早春二月,气温已经飙升至13摄氏度。北京到处沉浸在奥运来临的气氛中,各大IT厂商也纷纷搭上奥运概念,“科技奥运”为主题的活动愈加密集。 时光往回倒退13年。1995年8月的深圳,天气异常闷热。 在八卦四路刚开张不久的香港美食城里,两个中年男人相对而坐。 他们后来成为中国IT产业两个时代的分野。 他们中,一个是北京的大公司四通集团的总裁段永基,一个是深圳的小公司华为的总裁任正非。关于他们之间的交往,多年来外界一直没有机会了解。当时四通集团仍然是中国最大、最著名的民营科技企业,而华为的实际员工数只有800人。这是他们的第一次会面。在任正非心里,四通是个既神秘又令人羡慕的企业,段永基则是领导这个名震海外的企业的高人。 当时的任正非并不会想到,两年后,他会改称段永基为“败兵之将”;华为也从四通手中接过了飘扬了10年的民营企业“品牌”大旗。 硬件品牌:挥别民族情结 在改革开放激荡的30年中,有许许多多的中国品牌,留下了浓重的一笔,成为日后叱咤风云的民族企业代表;也有许许多多的中国品牌,只能享受昙花一现的短暂风光。 1984年被称为中国的“公司元年”,许多日后名噪一时的公司都诞生于此时。这一年,邓小平第一次南巡,在珠海挥毫题下“珠海经济特区好”;中央宣布向外国投资者开放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下海”成了民间最时髦的词汇。在“时不我待”的感染下,许多人觉得“干大事的时候到了。” 这一年,诞生了许许多多非常幼小的公司:原本倒卖玉米的王石当上了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的经理,他发现“倒汇”比“倒玉米”痛快;35岁的张瑞敏被派到青岛一家濒临倒闭的电器厂当厂长,将76台不合格的冰箱全部砸为废铁;四十不惑的柳传志告别了中科院计算所的清闲生活,搬进了中关村一间20平方米的小屋;李东生在一个简陋的农机仓库开辟了自己的工厂,与香港人合作生产录音磁带;还是这一年,李经纬把广东三水县酒厂的“中国魔水”带到了洛杉矶奥运会;史玉柱把自己关在屋里几天,写出了第一个统计系统软件…… 这一年,中国经济史和企业史都进入了一个拐点。这些微不足道的品牌,日后从各个偏僻的角落走到了市场之巅。1984年,几名中科院计算中心下海创业的科技人员,借款两万元办起了北京市四通新兴产业开发公司。当时四通的目标是:做中国的IBM。在1986年~1996年的10年间,四通的品牌曾是“打字机”的代名词,人们将买打字机称做“买四通”。鼎盛时期,四通打字机曾占国内办公自动化市场的85%;32家分公司、100多家培训中心、900多家维修服务中心和1280家销售代理商,这是当时全国独一无二的。但20年的品牌搏杀,四通的品牌已经成为反面典型。电脑时代的来临成为打字机历史的终结,四通败相已现,一次次丧失了东山再起的机会,只能通过不断多元化寻找新的业务增长点。 “四通的成功首先源于它的产品,而产品源于‘四通人’,‘四通人’又源于四通的文化,四通文化则最终源于企业家的思想。而它的失败路径正好是相反的过程。”曾任四通副总裁的李玉琢如此总结四通品牌的没落。“品牌不光是外在的,还有内在的。”北京BrandMan品牌顾问董事总经理梁虎指出,在企业形成品牌的过程中,品牌文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0多年前,如今车水马龙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是北京郊区的一片荒地。中国IT业由此诞生,并和几个满怀抱负的年轻人密切相关。1985年,张玉峰走出北大书斋办了自己的公司,起名叫“方正”;1988年,王文京从中央事务管理局辞职,创立了独立的软件公司“用友”;1989年,杨元庆从中科大研究生毕业,误打误撞去了一个叫“联想”的小公司应聘销售…… 经过近10年的代理之路后,联想已是行业老大,有强大的品牌影响力。但在当时,它的锋芒并不及在南方叱咤风云的“电脑巨人”。 1989年7月的深圳特区街头,一位浙大数学系毕业的安徽小伙子孤身而立,怀揣着耗费数月心血研发的M-6401桌面排版印刷系统软件,不知何去何从。两年后,中国电脑行业突然出现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巨人”,公司所销售的仅仅是一种提供文字处理功能的M-6402汉卡,却瞬间编织起了一张当时电脑行业最大的连锁经销网络,巨人汉卡的销量一跃而居全国同类产品之首,“巨人”品牌一夜成名。 从1992年开始,巨人赫然成为中国IT行业的领头军,集团资产过亿、年销售量同比增长300%,每年回报3000多万元。巨人集团的子公司从38家发展到创纪录的228家,还斥巨资建造高达70层的巨人大厦进军房地产市场。作为改革开放的典范,史玉柱接过了“发展民族工业新经济”的大旗,从中央到地方的各大媒体整版地报道史玉柱的个人传奇经历和巨人的宏图壮志。 但事实证明,这可能是企业发展的一条歧途。研究巨人历史的书籍不胜其数,而相同的一个观点是巨人当时的发展战略明显超越现实,使它从一开始就陷进了自己画好的狭隘的民族经济陷阱中。而联想后来的发展路径则证明,PC行业的一个必经之路就是国际化。
巨人倒下后,中国IT发展的火炬渐渐从南方特区交接到了北方硅谷——中关村。中关村的创业者开始从卖汉卡升级到卖PC整机,涌现出恒生、柏安、沐泽、八亿时空等一批名噪一时的本土品牌。但随着欧美向中国计算机出口的禁令失效,康柏、惠普和IBM等著名国际IT品牌纷纷进入中国市场,此后10年的价格战使绝大部分本土品牌纷纷倒下,存留的品牌也多失去了曾经的风光。 “在充分和完全的市场竞争中,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不可能长久维持,只有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转化为品牌竞争力,无论是民族经济还是国际化企业,才能长治久安。”一位退出PC行业的IT老人如此解释自己当初的困境,他死活不愿意再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报道中。 通信品牌:大喜大悲 如果四通曾代表中国IT的硬件时代,“巨大中华”的崛起则是中国进入软件时代的最好见证。而在通信业中,巨龙通信则是曾经极为辉煌的品牌,显赫时期它曾经占据了中国交换机市场的半壁江山。 1997年被称为“崩溃之年”。不同领域的一批品牌在这一年同时崩溃,巨人大厦停工、瀛海威迷失方向。但另一批企业,联想、海尔、长虹等高举民族品牌旗帜,在消费领域捷报频传;丁磊、张朝阳、王志东呈现互联网品牌铁三角。同时,中国通信业风生水起。 上世纪90年代初,人们忽然发现街道两边越来越多地出现了“程控电话,长途直拨”的广告语。当时国内程控交换机市场有来自7个国家8种不同制式的机型,不仅互联互通复杂,通话质量低下,产品进口价格也十分高昂。 1995年,由数家国有企业发起的巨龙公司成立,为中国通信业带来一缕春风。巨龙“04机”是中国第一台大型数字程控交换机,它打破“七国八制”对市话市场的垄断,降低了交换机的价格。自1991年12月通过邮电部技术鉴定之后,在电信数字局用交换网业务中占据了长达10年的主力位置。 1996年,以当时通信制造领域最好的几家企业巨龙通信、大唐电信、中兴通讯、深圳华为为代表的民族通信厂商,纷纷推出自己的万门机产品,在市场上全面突围。“七国八制”成为历史,“巨大中华”一跃成民族电信制造业的代名词。到1998年,这4家企业利润都过亿元,其中最多的华为销售收入89亿元、巨龙30亿元,最少的大唐也超过9亿元。 作为“巨大中华”之首,巨龙并未利用好它最大的资本。当接入网、光传输、无线通信、宽带光纤网络等新技术袭来时,巨龙没能把握机会。决策失误导致了市场销售的下滑及日后公司资金、人才、技术等多重危机,为此巨龙先后进行了多次机构调整和重组,但收效甚微。国外有思科,国内有华为,“巨龙内部承受的压力,是外人无法想像的。”一名巨龙员工如是说。 如今,四强今非昔比,“巨大中华”也不再被提起。百度搜索上,“巨龙”系企业一张A4纸张都写不完,但人们已无从分辨哪一条才是当年推动中国第一台万门程控交换机产业化的“巨龙”。经过10年的大浪淘沙,巨龙产品彻底退出了电信舞台。巨龙起了民族通信制造业崛起的头,最终却没有跑过“大中华”。 维杰伊·韦斯瓦纳斯和乔纳森·马克1997年在《哈佛商业评论》中发表了一篇名为《品牌经营的最佳战略》的文章,文中首次提出了低路品牌和高路品牌的概念。他们认为,品牌的盈利能力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即市场份额和这类产品的性质。品牌战略的选择是有条件的,不同的企业应根据不同的变量选择不同的战略。
第1页/共4页 <<上一页 | 下一页>>
巨人当时四通巨龙